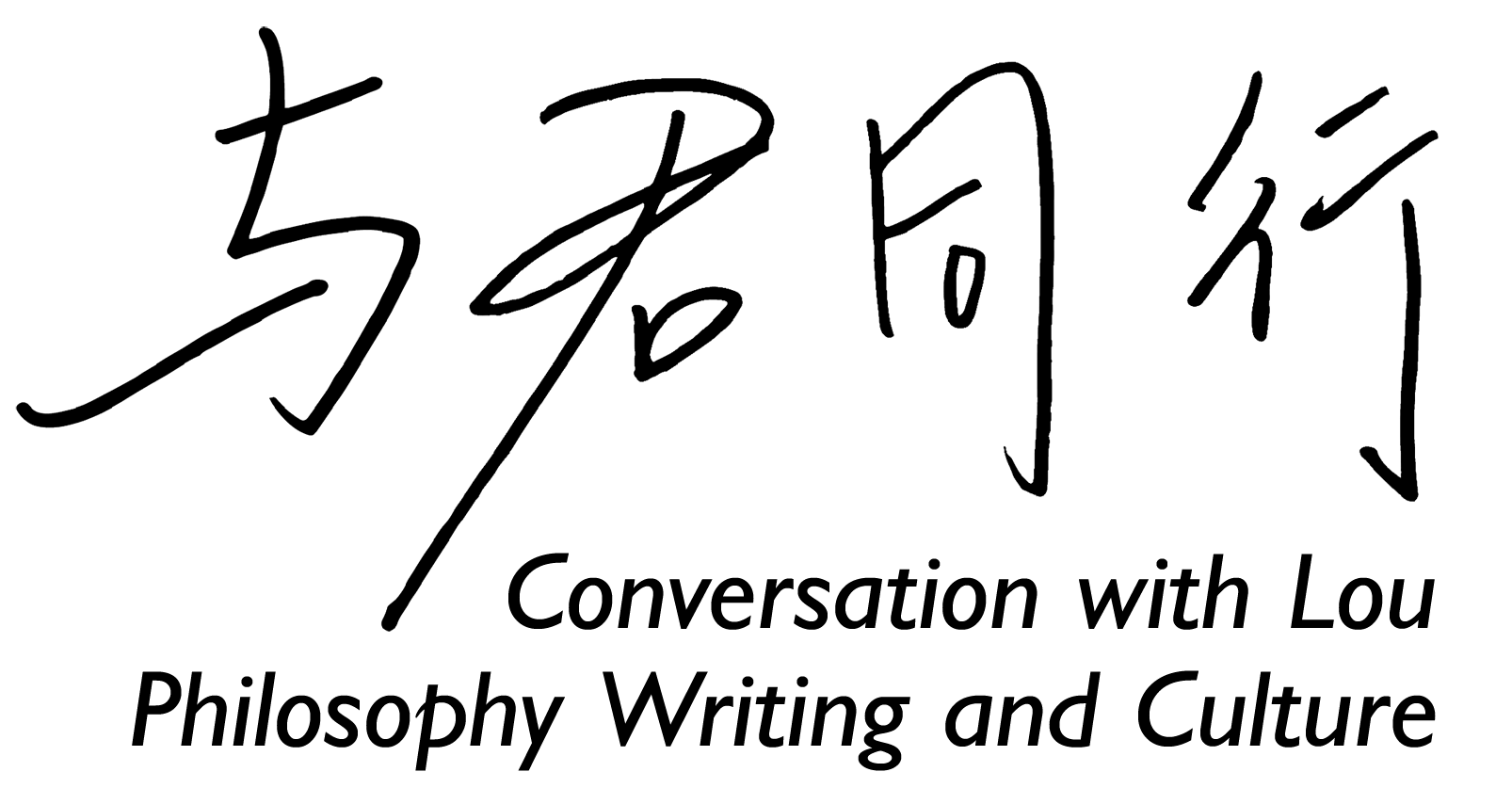娄林 (xianhua.lou@connect.polyu.hk)
来香港读书已经有近三个月了,每日都从大围站坐车到红磡往返,香港交通价格高,因此不敢去远的地方,三个月总共只去了四次香港岛,因为港铁收过海费。东铁线偶尔有意外情况发生,多是旅客进入铁道范围等情况,潮湿炎热的天气下,在两个据点之间来回奔波,行人多少带些疲惫,压力也像涌动的人潮一样密集,不像湖北,香港没有特别能够静下来的地方,郊野公园除外。
香港住宿很贵,我租的一个下铺床位,床板是坏的,没人管,一个月也要3600港币,水电费也很贵,因为要交押金。我自己的小桌子在室外,室内的桌子是上铺的,室友刷抖音,玩游戏的时候声音外放到晚上11点半,因此做作业都要到学校图书馆待到11点钟。学校的图书馆安静区,偶尔有人谈话,一直不停,这片土地似乎是热闹的,看到窗外翠绿的树,想起潜江灰蒙蒙的天空,虽然是一座不大为人知的城市,但我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我能够休息,安静的一个人呆一会。
香港的地铁上,如果不是安静区,常常听到人谈话,吵吵闹闹的人间。昨天夜晚,从香港理工大学的天桥走到地铁站,听到尖锐的笑声,好像是一些女生,在谈论一些青春时期的话题,人来人往的地铁站,苍白的灯光,却找不到一个能够休息的地方。
在《巴黎评论》采访中(Gobeil, 1965),波伏娃坦言自己不是一名好的教师,因为好教师需要关注所有学生的需求(好学生与后进生),但她坦诚她只对好学生感兴趣:
“because I was interested only in the bright students and not at all in the others, whereas a good teacher should be interested in everyone. But if you teach philosophy you can’t help it. There were always four or five students who did all the talking, and the others didn’t care to do anything. I didn’t bother about them very much.”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好的教师)因为我只对好学生感兴趣,然而,一名好的教师应该对所有的学生都感兴趣。但是当你教哲学的时候,你无法做到这一点,一堂课上,这里总是那四五个学生在参与课堂互动,而其他学生根本都不在乎课堂内容。我并不特别在意这些。”
de Beauvoir, 1965, The Paris Review interview
波伏娃与西蒙娜·薇依一样,都曾担任过哲学老师,好似当今文人的出路都是教书。桑塔格说文学是心灵的教育,让人认识到人的可能,并且去明白是非善恶,可如今的世界,这个荒原一般的现代世界,生长在地上的都是钢筋混凝土的楼房,人们关注金钱与利益。每次回到住所,大堂的女士都微笑着跟我打招呼,我很感动,也笑着说谢谢,特别疲劳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也感到一丝慰藉。在潜江,这些小礼节已经渐渐淡忘,人们的言语有些赤裸裸,面色中多一些冷漠,好似只有权贵人士值得被优待,失去的灵魂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在大围,走到天桥下的电梯口,路口突然闪来一位骑单车的外送员,他带着头盔,大约有五十多岁了,香港人一般偏瘦,他也是,他对我道歉,广东话的sorry,我没反应过来,可能是太久没有被这样礼遇过,突然内心一阵心酸,心中的一句“没关系”还没来得及说。香港这片土地上,承载了许多微小的善意,我好想保留它。
Reference
Gobeil, I. B. M. (1965, Spring-Summer). The Art of Fiction No. 35. The Paris Review, issue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