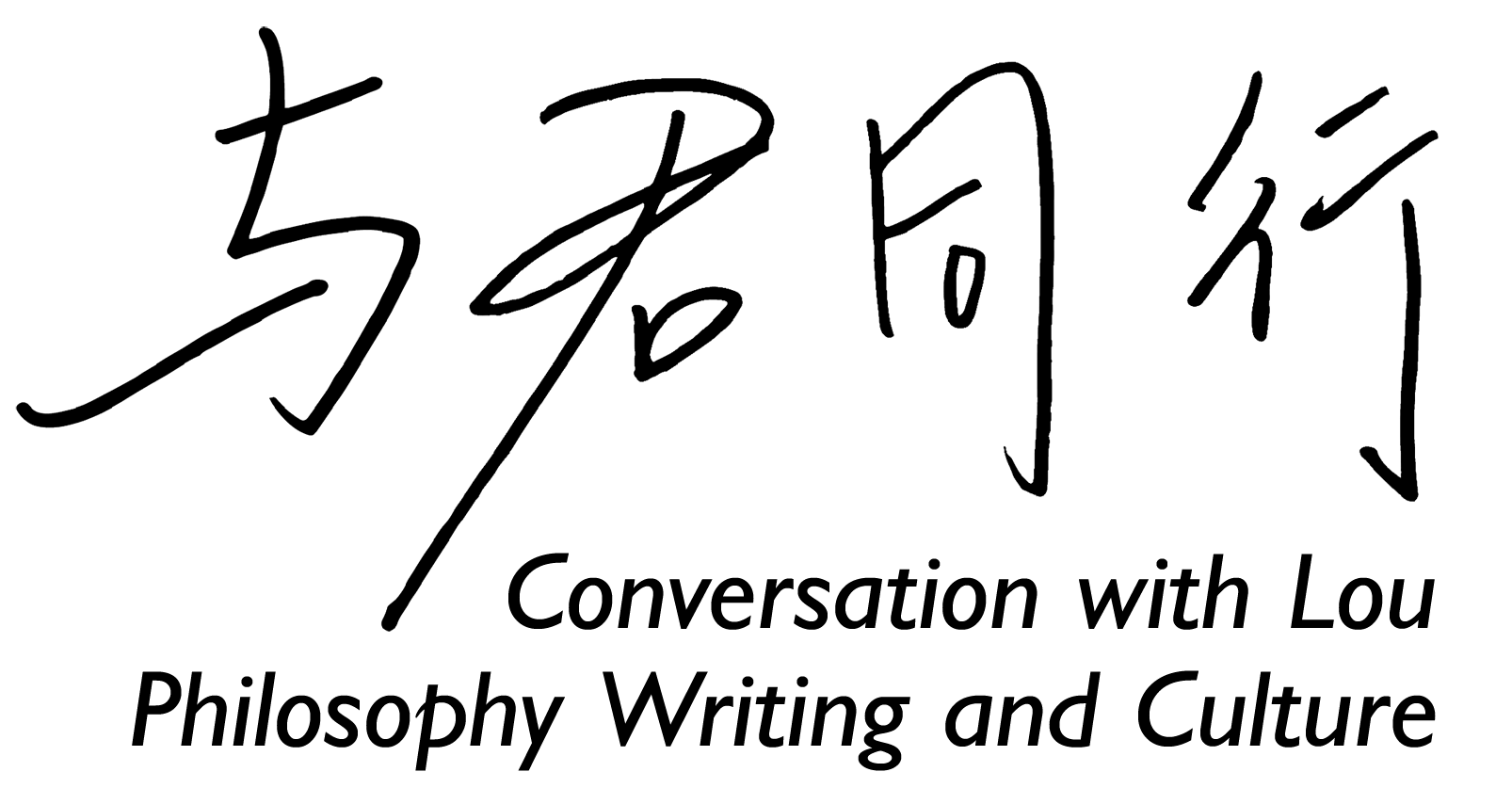“情愿过夏天,总比冷天穿太多强。”在北京的时候,有新闻媒体报道是最热的记录。“倒是赶上了记录。”溪对我说。总知道确实的热,但怕晒伤还是穿长袖长裤。路人倒没有惊奇。出故宫,有外客在景山公园问“是否需门票”“是”。溪不想上山。“你去,我在山下等你。”一脸期待。景山有粗旷的地方,差点摔下来,我拍了几张照片,和其他中国的山丘并不不同,安静干枯。虽然40多度,却没太热,与干燥有关。
出颐和园的地铁站时,有韩国旅行团从身边经过,溪搭在我的肩膀边走路,是干燥的热,只要喝水就能忍住,韩国人来中国旅行似乎都带宽檐帽,凉鞋。针叶林的花坛没有树荫,颐和园外有点像沙漠。“你会忘记我吗?”正是夕阳下山的时候,人来人往的石路上,“不会。”我答到。
溪喜欢看航拍中国的纪录片,总叫我也看,“真漂亮。”他喜欢看漂亮的酒店和名人的房子,也许是想安定下来,像海子的诗里写的一样。倒也是,喜欢看海子与顾城的诗,有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精神,但他们的精神世界都不太愉快,连浪漫派的德国诗人也是。看美国有作家写艺术家作为苦痛的榜样,不禁惘然若失,一笑。有次在电视听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虽是在平常不过的话,但觉得也很平实。“我曾看过一个纪录片,是一位独身的老人,虽然坚强,可我看了很伤心,我不能一个人。”溪对我说。
路过使馆区,有家波斯餐馆,人来人往,各国旗帜飘扬,错以为在古代的长安。其实我也怕。看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农村的孤寡老人,照片中神色暗淡,也不难想他们觉得“让美国再次伟大”是最后希望,虽然是最道地的民族精神,可人总需要一种依靠。
喜欢坐公交车,看车窗外行人来来往往,正在最美的年纪,歌曲在最美的片段,戴着墨镜,留下的眼泪也不太担心。“有多少恨就有多少爱。”宇喜欢唱五月天的温柔。大学寝室可以看到天主堂的十字架,上坡路,每次归途,都像登山,反倒很快乐。
大学在郊外,去市中心需1个小时,反倒像去另外的城市,每次归途,车上的人都睡眼朦胧。宇喜欢听张悬的《宝贝》。“我要窒息了,车上的人都不开窗。”虹林对我说,是冬天的时候,没人开窗,怕冷。末班车,下车的话,后果不可想象,荒山野岭,长路漫漫,不知归途。“我要下车了,不然我活不下去了。师傅,下车。”虹林不停的喘气,终于好了些,“实在是忍不住”她回过气来,“办法比困难多,”她说道。拦了面包车回程,车上寂然,拥挤,汗味,算最本真的生活,虽然冒险,却很快乐。有次在归程的末班车上听到《宝贝》是宇最喜欢的歌,起初以为是谁的手机响了不接,后来才知是汽车广播,但车上没有人做声,路过的街灯明明暗暗,像最粗糙的蒙太奇,却是最震撼的画面,我看着车窗上自己的倒影,以为青春可以永远都在,是最痛苦的梦想,因为不想失去它,所以这一刻永远都记得。
“喜欢年轻的时候还是年老的时候?”“这是什么问题,当然是年轻的时候。”我的祖母听到这问题,微笑着说。“老了就是精力不及从前了。”最喜欢夏天,是精神最好的时候。海明威记忆中的非洲,阳光明媚刺目,狮子在海岸徘徊。